祝谦
20世纪90年代,我在中央媒体工作,新疆大地上风起云涌的变迁,蕴含着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。我在一些故事里,“扮演”着亲历亲为的角色。尽管时间已经久远,但那些人和事,仍栩栩如生,萦怀于胸,鲜明且深刻。
“黑”“白”两色交相辉映
1995年8月的一天下午,我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“串门”,偶然碰到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部长,他把我邀到办公室,一落座就急忙告诉我,当天上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研究新疆经济发展,提出要抓牢两个字:黑、白。工业抓黑色产业:石油、天然气;农业抓白色产业:棉花。会上经过充分讨论,作出决定,新疆经济发展战略:一黑一白。
我听了以后,欣喜有加。当时,我正为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报道抓选题,苦于找不到重大主题的切入点,难以落笔。这黑白二色,使我茅塞顿开。媒体人都知道,新疆大地的重要“收藏”:已探明石油资源储量占全国首位,天然气资源量居全国第二位。当时,石油已占新疆工业产值的30.5%,比重还在增加;棉花已占新疆农业产值的41%,涨幅还在攀升。过去的积累、思索,迅速聚集到黑白二色旗下,一篇《黑色的崛起,白色的辉煌》的通讯,加以副题“新疆经济腾飞的新格局初步形成”很快完稿。
9月20日,《人民日报》以庆祝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40周年的开篇文章,加上栏题,在头版头条刊出。这是新疆“一黑一白”发展战略见诸媒体的第一篇文章,而且,一见报就上了《人民日报》的头版头条。很快,从中央到地方,从干部到群众,从海内到海外,大家都知道新疆的“黑白”战略。
时至今日,后续产业蓬勃兴起,但工业的石油、天然气,农业的棉花,仍发挥着扛鼎之力。“黑”“白”两色,就此交相辉映。
远去且末的那条路
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缘的且末县,曾是古且末的都城,距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州府库尔勒市800余公里,是巴州管辖最远的一个县,这州县距离远得令人有点惊讶。谁知,更令人惊讶的,是我听到的那个故事。
那是1995年4月的一天,我陪同且末县委书记去拜访一位老干部,他叫吾甫尔·艾则孜,是一位退休的税务局长。吾甫尔是一个很风趣的老人,谈起且末,可能是刻骨铭心,他总爱讲且末的路。他乐呵呵地说,他1952年参加工作,在县里当税务员,当时总共3个人,管着全县的税收。那时的专员公署在库尔勒以北的焉耆,去焉耆开会,是骑毛驴,从且末到库尔勒,紧赶慢赶,28天,再一天赶到焉耆。一趟下来,屁股上磨出厚厚的老茧。
“一路怎么吃饭、睡觉、喂驴呢?”
吾甫尔说,在这条丝绸古道上,大约30公里左右,便有一处无人驿站,供行人歇息,有些大站,还备有炊具。长途跋涉的,大都是出公差的人。一个人两头毛驴,一头是坐骑,一头驮行囊。到了有人烟的地方,补充一次给养,就这样一站一站朝前蹭。不能多走,也不能少走,过了站或不到站,就会有危险。一路上看不到飞鸟,也见不到走兽。若不在站里,一旦碰到缺水、酷热、严寒、沙尘暴和疾病,就会有十命九不保的灾患。
有点耸人听闻。我不解:“骑马不是快些吗?”
“马是快,但缺耐力,一趟走不下来,它就死了。”吾甫尔说,毛驴是最好的交通工具。
“开会怎么通知呢?”
“一个月以前发电报。”
吾甫尔告诉我,1957年,且末县通了汽车,如果路上不出故障,汽车得走一个星期。那时的路况差,汽车都得带着木杠子,碰到沙窝,得搭上杠子,汽车的双轮卡在杠子上才能通过。吾甫尔从皱着眉头说到眉开眼笑:
“且末这条路上的故事,我能给你们说一个星期。不过,最动听的,还是这个最新的故事:1991年夏天,我坐上从且末到库尔勒的飞机,飞机像一只大鸟,扇着翅膀,在沙漠上嗡嗡地叫着,晃呀晃,我像做梦一样,一步没有动,800多公里‘走’完了。82分钟,轰地一声,到了。过去得走28天,屁股磨出老茧,如今,屁股还没有坐热呢。”
我们一行人,开怀大笑。吾甫尔的故事,艰辛、沉重,却又坚韧、刚强,前进的足迹,步步闪光。
今天,且末县不仅柏油路通到乡村,还通了火车,扩建了机场。远去且末的那条路,留在历史记忆里的,是一个值得回味的幸福剪影:28天、7天、82分钟。
“我们喝上了幸福水”
过去,新疆有些地方农牧民常年喝着不卫生的涝坝(蓄水的土坑)水、河渠水、氟超标的浅层地下水,人畜共饮,时常发生与水质相关的传染病、地方病,对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产建设造成严重影响,长期不能摆脱贫困局面。
1994年8月,全国政协领导到新疆考察,26号到和田县布扎克乡,他站在一个涝坝旁,看到那不断泛着气泡的浑水,极为焦虑和关切。他问站在身边的和田县领导:“和田县有多少个行政村?”
“有400多个。”
“2万块钱打一眼井行不行?”
大家一愣,犹豫了一下,觉得可能有投资,七嘴八舌地说:“行!”
“好!你们要拍胸脯,一年为限,明年8月验收。”全国政协领导接着说,按500个村算,1000万元。政协没有钱,但有一个“协”字,可以协商社会各界,大家出力,把这件民生大事办好。
10月5日,中央统战部领导带着1500万元的银行支票,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了交接仪式。统战部、工商联,各界人士踊跃捐赠,筹集到的这笔资金,为新疆在和田县改水防病启动了先行试点。
两万元能打一眼井吗?我问同行的人,懂行的人都摇头,说按当时的价格,最低也得四五万元。和田县的领导们是怎么盘算的呢?
1995年9月,国务院领导到新疆考察工作,并专程到和田县察看改水防病工程。也在布扎克乡,他看到废弃的那个涝坝旁,建起了一座簇新的供水站和水塔,可供周围31个自然村、5114人、12113头牲畜饮水,投资48万元。农民投工投劳,挖入户沟道,每户仅出资约100元,自购水管。初略一算,恍然大悟,当时县领导们如此爽快承诺,就是这么“解题”的。
9月9日这天,像一盛大的节日,兴高采烈围上来的维吾尔族农民,纷纷向国务院领导报告:
“我们喝上了幸福水!”
“自来水,亚克西!”
国务院领导来到一户维吾尔族农民家,拧开水龙头,清亮的自来水哗哗流出。千百年来,人民群众喝涝坝水的历史结束了。在中国的农村,农家用上自来水,当时也是一个传奇。
在中共中央、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,解决防病改水资金3亿元,新疆自筹资金3亿元,各种捐赠3亿元,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奋斗,建成水厂1200多座,打机井1000多眼,建水塔600多座,高位水池200多座,铺设饮水管道3.1万多公里,解决了400多万人、1400多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。从此饮水无忧,告别涝坝水,这是千百年来的一个历史奇迹。
群众自发地在不少地方立了改水防病纪念碑,碑文表达了农牧民的心声:“改水防病千秋伟业,造福边疆亘古丰碑”“今日喜饮幸福水,永世不忘共产党”。
(许庆光整理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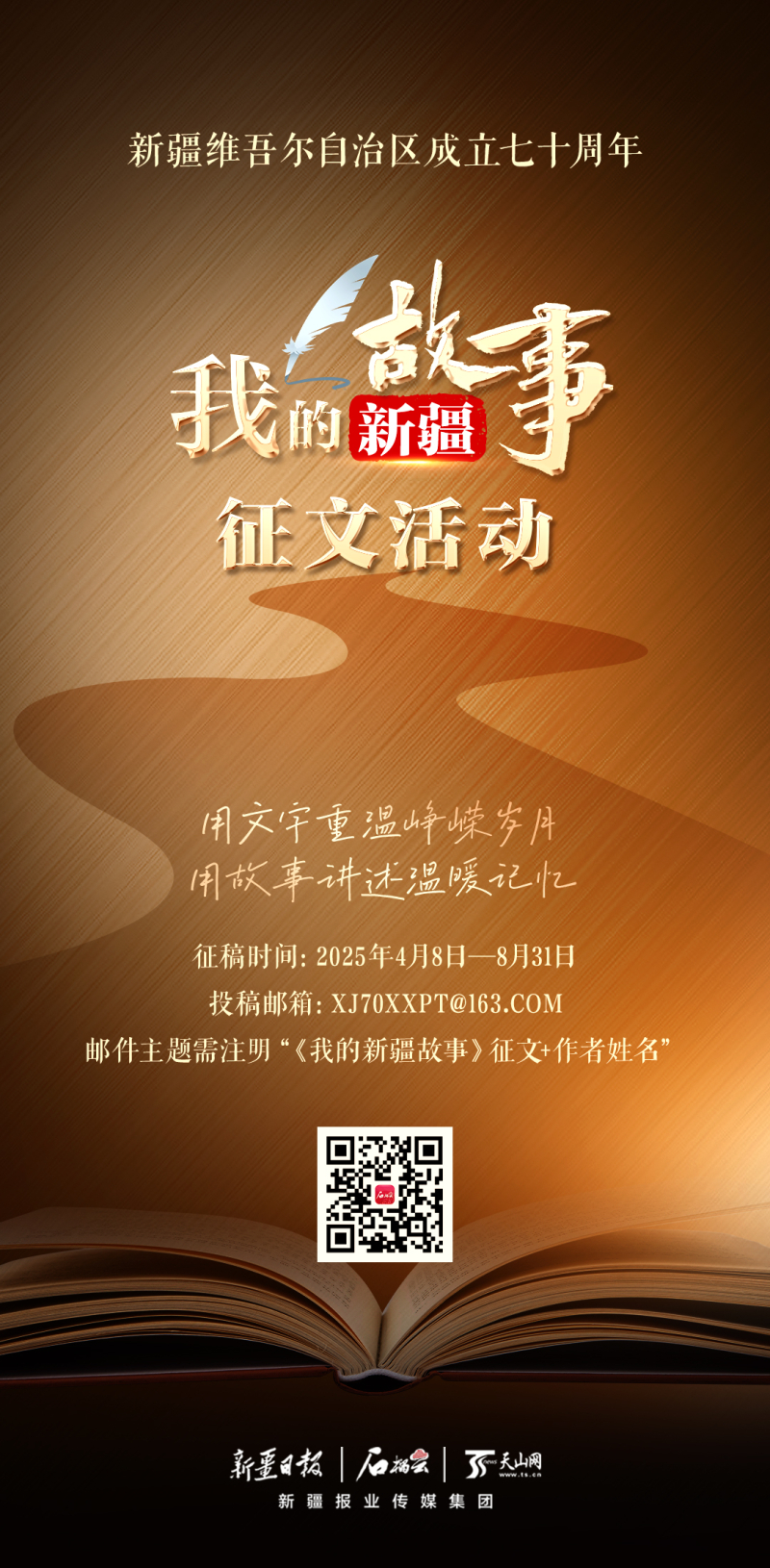
相关报道:
我的新疆故事⑧丨在新疆的每一天都是庆典 每一个新疆人都是一首诗
(版权作品,未经授权严禁转载。转载须注明来源、原标题、著作者名,不得变更核心内容。)




















最新评论: